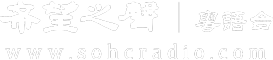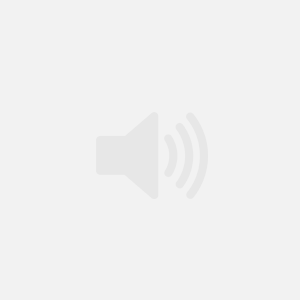
英國十九世紀政治家查士德斐爾爵士曾對他的兒子作過這樣的教導:“要比別人聰明,但不要告訴人家你比他更聰明。”蘇格拉底也在雅典一再地告誡他的門徒:“你只知道一件事,就是你一無所知。”
無論你采取什么方式指出別人的錯誤:一個蔑視的眼神,一種不滿的腔調,一個不耐煩的手勢,都有可能帶來難堪的后果。你以為他會同意你所指出的嗎? 絕對不會?因為你否定了他的智慧和判斷力,打擊了他的榮耀和自尊心,同時還傷害了他的感情。他非但不會改變自己的看法,還要進行反擊,這時,你即使搬出所 有柏拉圖或康德的邏輯也無濟于事。
永遠不要說這樣的話。“看著吧!你會知道誰是誰非的。”這等于說:“我會使你改變看法,我比你更聰明。”——這實際上是一種挑戰,在你還沒有開始證明對方的錯誤之前,他已經準備迎戰了。為什麼要給自己增加困難呢?
一位年輕的紐約律師。他最近參加一個重要案子的辯論;這個案子牽涉到一大筆錢和一項重要的法律問題。在辯論中,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對年輕的律師說:“海事法追訴期限是6年,對嗎?”律師楞了一下,看看法官,然后率直地說:“不。庭長,海事法沒有追訴期限。”
這位律師后來說:“當時,法庭內立刻靜默下來。似乎連氣溫也降到了冰點。雖然自己是對的,但自己是錯了;自己如實地指了出來。但庭長卻沒有因此而高興,反而臉色鐵青,令人望而生畏。盡管法律站在律師這邊,但自己卻鑄成了一個大錯,居然當眾指出一位聲望卓著、學識豐富的人的錯誤。”
這位律師確實犯了一個“比別人正確的錯誤”。在指出別人錯了的時候,為什麼不能做得更高明一些呢?如果有人說了一句你認為是錯誤的話,你這樣說不 更好嗎?“唔,我倒有另外一種想法,但也許不對。我常常弄錯。如果我弄錯了,我很愿意得到糾正。”這將會收到神奇的效果。無論什么場合,試問,誰會反對你 說“我也許不對”呢?
其實,那才是科學的做法。有一次,有人去訪問著名的探險家和科學家史蒂文生。他在北極圈內生活了11年之久,他告訴他人正在做一項實驗。我問他: “史蒂文生先生,你打算從實驗中證明出什么呢?”他回答,他說:“科學家永遠不會打算證明什么。他只打算發掘事實。”
那位因為正確而犯了錯誤的律師,如果懂得史蒂文生的思考方法,他就一定會使法官的態度寬容大度起來。
我們不少人都犯有武斷、偏見的毛病,我們不少人具有固執、自負和嫉妒的缺點;一般都不愿改變自己對事物的看法。
羅賓森教授在《下決心的過程》一書中說過一段富有啟示性的話:
“人,有時會很自然地改變自己的想法,但是如果有人說他錯了,他就會惱火,更加固執己見。人,有時也會毫無根據地形成自己的想法,但是如果有人不同意他的想法,那反而會使他全心全意地去維護自己的想法。不是那些想法本身多么珍貴,而是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威脅……。”
可見,對方處理得巧妙而且和善可親,我們也會承認自己的錯誤。但是,把難以下咽的事實硬塞進我們的食道里,結果就適得其反了。
如果你還想知道一些有關做人處世、控制自己、加快人格成熟知識的話,不妨看看本杰明?富蘭克林的自傳。他在自傳中說:“我立下一條規矩,決不正 面反對別人的意思,也不讓自己武斷。我甚至不準自己表達文字上或語言上過分肯定的意見。我決不用‘當然’、‘無疑’、這類詞,而是用‘我想’。‘我假設’ 或‘我想象’。當有人向我陳述一件我所不以為然的事情時,我決不立刻駁斥他,或立即指出他的錯誤;我會在回答的時候,表示在某些條件和情況下他的意見沒有 錯,但目前來看好像稍有不同。我很快就看見了收獲。凡是我參與的談話,氣氛變得融洽多了。我以謙虛的態度表達自己的意見,不但容易被人接受,沖突也減少 了。我最初這么做時,確實感到困難,但久而久之,就養成了習慣,也許,50年來,沒有人再聽到我講過太武斷的話。這種習慣,使我提交的新法案能夠得到同胞 的重視。盡管我不善于辭令,更談不上雄辯,遣詞用字也很遲鈍,有時還會說錯話,但一般來說,我的意見還是得到了廣泛的支持。”
其實,富蘭克林在這里并沒有提出什么新的觀念——這只不過顯示了他人格成熟的重要標志:寬容、忍讓、和善。
主持人:余慧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