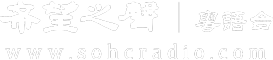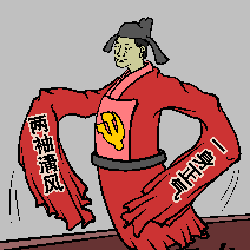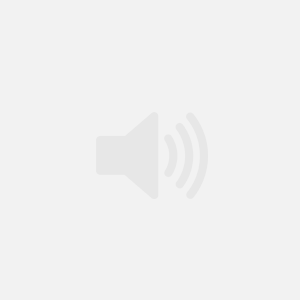
(2)老師的教法
不管這些課文的意思多么單純明確,但任何文本在理論上都可以用多種方式解讀。為了杜絕這種可能,中共的教育部門要求語文老師在講解完字詞句段章之后,再“畫龍點睛”地指出課文的“中心思想”,強制學生重復這些黨文化話語。比如上文提到的《小音樂家揚科》是小學五年級的課文,其中心思想是“舊社會剝削制度的罪惡”,老師要引導學生“懂得窮人的理想不可能實現,即使有才能,也要被埋沒”,要“激發學生憎恨剝削制度,同情勞動人民的思想情感”。
(3)考試的導向
升學考試是各級教育的指揮棒。考試的命題趨勢對于教師和學生具有巨大的導向作用。也就是說,教學的重點受試題引導,而試題直接受制于中共政策。以高考作文題為例,1958年的全國題目是“大躍進中激動人心的一幕”,1977年的北京題目是“我在這戰斗的一年里”,上海題目是“在抓綱治國的日子里”。近年的作文題目中這種赤裸裸的黨文化題減少了,代之以比較隱蔽的黨文化,比如“一分為二”的所謂的“辯證法”。1990年的“玫瑰花有刺”又讓國人重溫了一把中共的經典自辯詞:“主流是好的”,“成績是主要的”,“成績是九個指頭,失誤是一個指頭”,“太陽和黑子”。而1991年的“近墨者黑”和“近墨者未必黑”,其潛臺詞是改革開放并不違背四個堅持,預示著1992年鄧小平南巡重新啟動跛足經濟改革。
升學考試對于各級教育具有絕對的導向作用。中共控制了考試的命題權,就是支配了學生學習時間的分配和腦力的運用。中共把要強制灌輸的東西作為考試重點,學生不得不花十幾倍、甚至幾十倍于學習其他內容的時間記憶那些黨文化內容。結果就是,黨文化象刀刻一般深深地寫進入了學生的心靈。
(4)新近的趨勢
曾幾何時,小學生的人生第一課就是“毛主席萬歲”,“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現在的課本“進步”多了,到了小學一年級下冊才羞答答地推出“鄧小平爺爺植樹”。杜甫的名句,“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不是直接寫詩人對孩子的想念,反而說小孩子還不懂得想念父親,角度新穎、情味雋永。現在的語文課本,很多課文都是用這個技巧編造的。小學生不需要喊“四個偉大”了,卻要和“鄉親們”深情地回憶,“吃水不忘挖井人,時刻想念毛主席”。以前鼓吹自己是“世界革命中心”,現在講述這樣的故事:留學生海外漂流遇險,想拿大衣換一塊面包,老板(西方人)不肯。可是看到學生脖子上的一面五星紅旗,“老板眼里閃出亮光”,非要用面包換紅旗。留學生大義凜然,拂袖而去,老板于是深受教育。政治課宣講“一個中國”,“不排除使用武力”,語文課則從臺灣沒有雪講起,最后用老師的話點題:“那里(北京)的小朋友正盼著你們去和他們一起玩呢!”
這套新近出版的小學語文課本從第二冊開始,系統灌輸“紅領巾”、“十月一日——祖國媽媽的生日”,用故事講述中共的臺灣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經濟政策,等等,思想單純的少年兒童在不知不覺中吸收了大量黨文化內容。
現在的語文課本加入了很多有時代氣息的作品,但我們必須看到,語文課仍然承擔著相當重要的灌輸黨文化的功能。這是因為,第一,黨魁文章仍然占據一定篇幅。第二,與眾多文學名篇并置在一起,黨文化篇目也自然獲得了文學名篇的地位,也就是被“經典化”了。當學生用這些黨文化篇目學習文法和修辭的時候,已經把內容當成自然、當然、甚至必然的東西,毫無戒備地吸收了。第三,目前應試教育中的技術至上化傾向把學生的注意力吸引到大量無謂的細節,對文章內容既無興趣又無能力探究。
當然,語文課是和其他課程配合發生作用的,語文課在一定程度上的“去政治化”,從另一方面表明黨文化的強大吸納力和高度欺騙性。就像“人權入憲”、江澤民提出“以德治國”、胡錦濤高呼“和諧社會”一樣,沒準兒哪一天,“堅持發揚儒釋道國粹”也會寫入黨章和憲法,繼續為“偉光正”和“與時俱進”提供注腳。
中共教育體制下的其他課程,像地理、音樂、自然科學等等,都同樣擔負著灌輸黨文化的使命。窺一斑可見全豹,這里就不詳細闡述了。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黨文化教育危害最大的不是灌輸的具體內容,而是灌輸給學生的認識世界、解釋世界的認知框架。學生把這個認知框架內化以后,從此對該框架無法處理的信息或者采取極端排斥的態度、對該框架無法解釋的現象視而不見、不聞不問,或者用中共灌輸的扭曲思維方式對這些信息進行加工,最后得出有利于中共統治的結論。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今天的中國人一方面很有思想、能言善辯,另一方面極端偏狹固執,對自己不喜歡的事物深拒固閉,滿足于一種“有選擇性的無知狀態”。
中國自古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說法,社會對教育普遍非常重視。對于為數眾多的農家孩子來說,考大學更是除參軍以外改變自己農民身份的唯一途徑。可是,中共掌控了一切國家資源,孩子們要么不受教育,要么就只能受黨文化的教育。幾十年來,中共把本來應是天下公器的教育變成販售自家私貨的作坊,一代代中國人被迫吞咽下黨文化教育的苦果。
5. 利用多種文藝形式灌輸黨文化
共產黨認為文藝是上層建筑的一部分,只能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中共奪取政權以后,從經濟上把文藝演出團體收歸國有,從組織上把文藝界人士變成“體制內人”并對他們實行思想改造,在創作上對文藝界耳提面命嚴密控制,在短時間內把所有的文藝形式,如電影、戲劇、歌舞、曲藝等,都變成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和灌輸黨文化的工具。
1)利用電影灌輸黨文化
(1)“電影是最重要的藝術”
二十世紀初興起的電影作為一種全新的藝術和娛樂形式,與傳統藝術形式相比,具有很大的優勢,迅速在社會上普及開來。嗅覺靈敏的共產黨很早就注意到電影。列寧說:“電影是教育群眾的最強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的藝術中,電影對于我們是最重要的”。1949年8月,中共宣傳部發布了《關于加強電影事業的決定》,指出:“電影藝術具有最廣大的群眾性與最廣大的宣傳效果,必須加強這一事業,以利于在全國范圍內,及在國際上更有力地進行我黨及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宣傳工作。”1951年,中共奪權后第一個思想改造運動從批判電影《武訓傳》開始,毛澤東親自捉刀,對《武訓傳》進行高調批判。毛澤東此舉預示著其后的中共歷任黨魁都對電影這一藝術形式格外重視。1953年,對電影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全部完成,早于對其他民族工業的改造。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中共把電影生產納入第一個五年計劃,對電影進行行政指令性管理。
從1949年到1966年間,中共總共拍攝了700多部故事片,全面編造“歷史選擇了中共”的謊言、圖解中共各個時期的政策、正面烘托黨代表人物、貶低傳統文化和傳統人物。這個時期的代表作品有《白毛女》、《鋼鐵戰士》、《南征北戰》、《青春之歌》、《紅旗譜》、《地雷戰》、《地道戰》、《李雙雙》、《紅日》、《小兵張嘎》、《英雄兒女》、《野火春風斗古城》、《霓虹燈下的哨兵》等。
在這些影片里,中共領導人、中共的所謂“英雄模范人物”、甚至心理陰暗、行為下賤的中共特務都成為被歌頌的對象。電影這種媒體形式使中共能夠“逼真地造假”,俊美的男女演員、詩情畫意的環境氛圍、傳奇般的或史詩性的情節設計,最大限度地達到了烘托黨代表人物的作用。人們心理上覺得藝術作品里的人物形象更“本質”、更具有普遍性,更有資格代表“黨”,殊不知他們看到的只是“黨”的假面具而已。
1949年以前,電影主要是一種城市藝術。為了擴大電影的宣傳范圍,中共以行政區為單位進行電影發行,系統建立電影放映隊,把宣傳觸角伸向農村和廠礦基層。1949年全國電影放映單位為646個,到1957年增加到9965個,其中電影院1030個,電影放映隊6692個。工會放映隊在1954年一年放映114000多場,觀眾達1.1億人次。這種電影放映隊一直活躍到八十年代中期,對普及黨文化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90%以上的“十七年”(1949年到1966年)電影被打成毒草,文藝領域成了樣板戲的天下。1979年,“十七年”影片被大量解禁,當年全民平均觀看電影28次,全國電影觀眾達293億人次之多。這種現象其實反映了中共的一個統治策略。在經濟上把人民剝奪到一無所有,所以只要經濟狀況略有好轉,人們就對中共感恩戴德;在文藝領域把人民剝奪到一無所有,人們就會對灌輸黨文化的宣傳品甘之如飴。
傳媒研究發現,一種媒體越是訴諸人的多種感官,越是容易取得較好的效果。電影作為一種藝術,綜合了文學、音樂、美術、表演等等,全面訴諸人的各種感官,是一種非常強有力的宣傳形式。中共在電影里塑造了大量的黨代表人物,他們的說話聲調、面部表情、肢體語言等等,成為人們、尤其是青少年模仿的對象,比如毛澤東在地圖前“指揮若定”的形象,蘇聯影片中列寧的演講動作等等。很多電影中的語匯進入人們的日常語言之中,例如電影《英雄兒女》中王成的臺詞“為了勝利,向我開炮”就一直流行到今天。電影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改變著人們的心理和行為模式,其效果之巨難以估量。
中共對電影的重視程度超過對文學的重視程度,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似乎越來越是如此。1989年之后,中共在意識形態上趨于收緊,1990年到1992年之間,在電影上出現了一個明顯的“主旋律”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