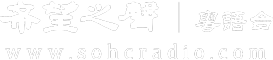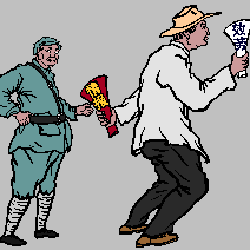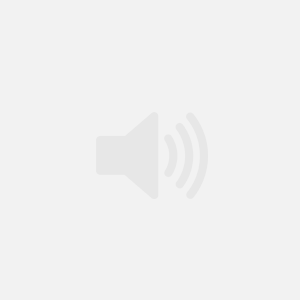
(2)主旋律與多樣化
八十年代以來,隨著中共的經濟改革,電影界也嘗試引入企業管理和競爭模式。目前中共大陸上映的國產影片中,大約25%是所謂“主旋律”影片,70%是娛樂片,5%為藝術片。然而,電影的宣傳功能并沒有被削弱,它只不過采取了更為復雜精致的形式。
首先,主旋律電影仍然承負重要的灌輸黨文化的職能。中共政策保證了主旋律電影的高投入、大制作、紅頭文件發行,各級組織觀看。《大決戰》投資數千萬元,拍攝地區涉及十三個省,參拍群眾多達十五萬余人次,中共對此的重視可見一斑。中宣部、中組部、國家教委、廣播電影電視部、文化部、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共青團中央等單位多次就主旋律影片的發行放映發出聯合通知,要求各級單位組 織觀看。《開國大典》、《焦裕祿》、《毛澤東和他的兒子》等影片的觀眾數量都相當巨大。
其次,主旋律電影向高科技化、精致化、人情化發展。八十年代以后,由于國門打開,觀眾的辨別力加強,中共從前編造的赤裸裸的謊言行不通了。中共的御用電影人揣摩觀眾心理,發展出一套復雜的主旋律策略。在所謂“革命歷史題材”的影片里,創作者刻意制造出記錄片的假相,把具有傾向性的對歷史的陳述假扮成客觀的歷史。戰爭影片注重大場面的表現,以逼真的戰爭幻像沖擊觀眾的理性判斷,使其不愿去分辨歷史與敘事。影片中的“革命領袖”被塑造成有血有肉的個人,以對他們的親情、愛情、友情等的呈現,拉近與觀眾的距離。“黨的敵人”也不復是以前電影中那副庸碌無能的模樣,他們被表現為有一定才華和人格高度的人物,但在歷史的較量中,敗在中共手下,以此烘托中共領導人的棋高一招。
《江澤民其人》中記錄了一件事,可以佐證中共主旋律電影手法的精致。江澤民曾應邀觀看電影《開國大典》。影片中的一些鏡頭讓他十分好奇,因為看起來像是極為珍貴的記錄片。江澤民問導演那些鏡頭是從哪里找到的。導演回答說,那些鏡頭根本就不是找的,而是他們剛剛拍攝的,經過特殊技術處理后,看起來就像記錄片一樣。江十分滿意,看完電影后總結說:“真的和假的糅合在一起——我都被騙過去了。”
中共的經典宣傳片的基調是偉光正、人物形象高大全。隨著它歷史上越來越多的罪惡被揭露出來,并且陷入一個又一個現實的困境,中共必須采取不同的宣傳策略為自己辯護。在有些影片中,中共領袖被塑造成雖具有崇高人格、但在無情而必然的歷史進程面前也無能為力的悲劇型人物,以求得觀眾對他們在歷史上犯下的罪行的諒解,同時使觀眾體會到普通人的快樂,從而更安于現存的社會秩序。
另外一個被廣泛采用的手段是“煽情”。電影《鄧小平》的導演聲稱:“我們必須把鄧小平的一系列偉大革命創舉,變成巨大的情感沖擊波,把一切理性的事件化為感性的情緒!”《焦裕祿》和《孔繁森》中都有大段的群眾性葬禮場面,用熒幕上群眾的哀哭感染劇院中的觀眾,使觀眾在被影片主人翁的“高尚道德”感動之余,認同他們所代表的“黨”的形象。
第三,娛樂片也同樣承擔著灌輸黨文化的職能。《電影通訊》1991年第五期評論員文章說:“作為一種創作精神,它(主旋律)不是一個量的概念,不是指多數作品與少數作品的關系,不是指這一題材與那一題材的關系,不僅不排斥任何創作,反而要求滲透于一切作品的創作指導之中。”
一些影片因為有娛樂片的外包裝,其中的黨文化非常隱蔽,觀眾在欣賞歷史傳奇、愛情故事、或感嘆視覺奇觀時,不知不覺地被灌輸了黨文化的觀念和趣味。電影《英雄》耗資2.5億人民幣,以美輪美奐的電影語言,謳歌獨裁強權和暴力征服;《漂亮媽媽》把下崗工人的悲慘遭遇歸咎于生理原因(女主人翁的兒子耳聾),間接掩蓋了中共政策失當造成城市工人大面積失業的事實;更多的影片編造故事,替中共煽動民族主義情緒。
第四,中共利用電影貶低傳統文化和傳統人物。經過長時間的黨文化宣傳灌輸,絕大多數中國人已經不知道傳統文化和傳統社會的本來面目。八十年代以來,很多電影人雖然力圖反抗黨文化,但因為他們本身在就是在共產黨的統治下長大,因此只能用黨文化的邏輯推想傳統社會的真實樣貌,因此很多影片中的傳統中國社會集封閉、壓抑、野蠻于一身,似乎還沒有中共統治之后的社會開化、進步。其實,這也是按照進化論那套邏輯推出來的,是在用另一種方式重復黨文化。
第五,無所不在的黨文化成為電影的審美風格元素,滲透于一切影視作品之中,利用觀眾的懷舊情緒,鞏固黨文化對人心靈的桎梏。
與其他藝術式樣相比,電影有自己的特點。比如,文學、美術、音樂表現什么、不表現什么,有很大的自由空間,而電影必須全面表現故事發生時的物質環境。因此電影畫面的背景和道具,都要經過精心布置,使它們能再現故事發生年代的典型環境。比如,表現文革時期的環境,要有毛像、大字報、綠軍裝、紅寶書等。1949年以后的中國,是共產黨一黨的天下。要想表現這一時期的典型環境,只能使用帶有濃重黨文化色彩的物品、聲音和場面。這些場景往往喚起觀眾的懷舊情緒,使觀眾覺得雖然那個時代有很多缺點,但畢竟自己曾經拚搏過一回,就像普希金說的,“那過去了的,就會成為美好的回憶”,過去的日子不管多么痛苦和荒謬,但人們那時還年輕,現在回想起來不免有一種浪漫的感覺。
充滿說教意味的影片在今天一般會招致反感,所以這種“順手捎帶”的方式,就成了影視作品在客觀上幫助中共灌輸黨文化的主要形式之一。這種勾起人懷舊情緒的電影元素往往是電影要表現的故事的背景;惟其如此,這些符號攜帶的信息才不會引起人們的警戒心理,暢通無阻地進入觀眾的頭腦之中。
影視(《激情燃燒的歲月》)、歌舞、文學、時尚、甚至廣告(北京中關村曾經有一個巨型廣告,仿照文革宣傳畫風格,上書“Internet就一定要實現”)、旅游(“紅色旅游”)等等都在加入這個“懷舊情緒”的大合奏,其實都是在幫助中共鞏固黨文化對中國人心靈的桎梏。
2)利用戲劇、歌舞、曲藝等多種文藝形式灌輸黨文化
中共的文藝宣傳形式,很多是從蘇聯生搬硬套來的。但是,因為灌輸黨文化的對象是所有中國人,中共必然利用一切民族文化資源,以適應不同人群的口味,使灌輸效果最大化。歌舞、京劇、話劇、評劇、豫劇、呂劇、越劇、粵劇、秦腔、秧歌、黃梅戲、花鼓戲、二人轉、京韻大鼓、河北梆子、山東快書、相聲、評書,中共無所不盜,黨文化附體在這些傳統文藝形式上,流毒可謂廣而且深。我們這里重點探討幾個相關的問題。
(1)附體在民族文化之上
既然中共給人民帶來了那么多的災難,為什麼有那么多“民歌”歌頌共產黨、毛澤東?這難道不是中共得民心的體現嗎?其實不然。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三天不見想死個人,呼兒嗨喲,哎呀我的三哥哥。”
1943年,這首陜北高原上傳唱數百年的情歌被重新填詞改編成《東方紅》,芝麻、白菜和豆角被置換成了東方、太陽和毛澤東,從此在中國大地上唱響,成為黨文化的“主打歌曲”之一。
類似的“借尸還魂”的例子數不勝數,比較有名的有把懲惡揚善、扶危濟困的白毛仙姑變成苦大仇深的白毛女,演繹“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主題。民歌劉三姐中的唱詞“塘邊洗手魚也死,路過青山樹也枯”原來是諷刺忘恩負義的狠心人,被篡改成“莫夸財主家豪富,財主心腸比蛇毒。塘邊洗手魚也死,路過青山樹也枯”,把劉三姐變成階級斗爭的先行者。形形色色的“新編歷史劇”利用古人的嘴,宣揚中共的世界觀和歷史觀,如《逼上梁山》,林沖“從恨高俅個人到恨整個剝削階級”:“要把這世界翻轉了,那須得槍對槍來刀對刀。”
經過三十年的文化滅絕運動、把優秀民族文化破壞殆盡以后,中共向人民和世界宣稱:它代表了正統的中華文化,同時更加肆無忌憚地打著傳統文化的幌子販賣黨文化的邪惡貨色。它所以敢更加肆無忌憚,是因為世界還不了解中國,人民多忘記了傳統。失去了敬神向善內涵的偽飛天、偽千手觀音和偽民歌民樂,伴著邪黨文人花言巧語、似是而非的詮釋,給中共的黑暗統治裝飾了一道華麗的花邊,同時更隱蔽、更徹底地摧毀人們對神佛的正信、變異了人們的道德觀念和藝術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