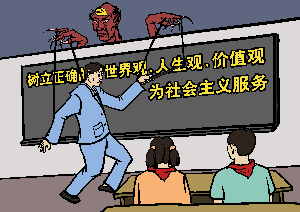3.利用邪黨的文人歌功惡黨
《九評之一》指出:“所有的非共產黨政權社會,無論其如何專制和極權,社會都有一部分自發組織和自主成分。……共產黨政權中,所有這些自發組織和自主成分被徹底鏟除,取而代之的是徹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權結構。”共產黨極端嚴厲的社會管制造成的后果之一是獨立的知識份子階層的消失。中共把一部分知識份子在肉體上消滅,把其他人編進各種各樣的“單位”之中。單位實際上是中共在城市對人民進行全方位管制的基本組織形式。知識份子喪失了不受政權控制的謀生方式和自由言論空間,無奈地淪為中共的附庸,在強大壓力下和走投無路中,他們中的大部分不得不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從各個角度、以各種方式歌頌邪黨,來保全性命并且養家糊口。中國社會素有“尊師重道”的傳統,中共政權利用民眾對文化人的信任和敬重,通過文人的著作和言論間接向民眾灌輸黨文化,改變中國人的善惡標準。建立并維持一個“偽知識份子”階層一方面使中共擺脫了“清議”和輿論的制約,另一方面使它能夠隨時隨地偽造出貌似公允的“科研成果”和“社會輿論”,為其邪惡統治辯護。
中共收編文人的主要方式包括:直接吸收他們入黨并加入政權(政府、人大、政協),比如郭沫若曾任中共國務院副總理,歷史學家吳晗曾任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長;把他們安置在民主黨派內;把他們安置在科學院(社科院)、大學或文史館等機構,或者安置在作家協會、戲劇家協會、文聯等部門。在文革中和妻子雙雙自殺的翻譯家傅雷是中共建政以后極少數不屬于任何“單位”的自由職業者之一。
為便于意識形態掌控,中共于五十年代進行高等院校的“院系調整”,把很多學校的哲學系合并一處。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等被稱為資產階級學科,被徹底取消,直到八十年代才逐漸恢復。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校、社科院、大專院校機構臃腫,人員眾多,打著“科學研究”的幌子,千方百計地替中共論證合法性。
經過組織收編、思想改造、暴力震懾、利益引誘、逆向淘汰(“反右”流放百萬敢言知識份子)等步驟,中共把所有知識份子攥在手掌心,少數正直而清醒的最多做到敢怒不敢言,膽小懦弱的只好隨風倒,奸佞諂媚的便主動投懷送抱,充當邪黨的爪牙和羽翼。
中共在哲學界、史學界、文學界、科學界、宗教界內都栽培了一些主要的代理人和吹鼓手。這些人平時裝模作樣,炮制出一篇篇文章、一本本“著作”,論證“馬克思主義是真正的科學”、“社會發展五階段是普遍真理”、“自然科學具有階級性”、“宗教是真理,社會主義也是真理”,充實黨文化的基本武庫。運動來了,這些人就如魚得水,用緊跟形勢向“黨”表忠心,用胡編亂造歌功惡黨、用斷章取義、深文羅織、無限上綱打擊中共的“敵人”,靠出賣人格從黨主子那里討一點殘羹剩飯。文化大革命中的梁效(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兩校學者組成的寫作班子)、八九民運后的何新、鎮壓法輪功中的何祚庥、于光遠、潘家錚等人,皆屬此類。
邪黨文人的代表,前有郭沫若,后有何祚庥。
被中共稱為“文化旗手”的風派文人郭沫若比變色龍還善于變化。中共讓他檢討他就檢討,讓他批武訓、批胡適、批胡風,他就批得比誰都起勁,讓他給哪個歷史人物翻案就給哪個歷史人物翻案。然而,原則立場不斷變化的中共讓郭沫若都覺得無所適從。文革初,郭沫若嗅出風向的變化,馬上檢討說:“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沒有學好毛澤東思想,沒有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自己。”
“政治院士”何祚庥,文革中為了諂媚毛澤東和共產黨,提出“毛子”和“無子”的概念,2001年又提出“量子力學的規律符合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精神”。就這樣一個科學痞子,成為中共打擊法輪功的主要“理論來源”。
正信、真理、和人類正統的道德體系都有穩定不變的特點。可以隨世俗權力起舞的道德根本就不配稱為道德,不斷“與時俱進”的真理從來不曾有資格被稱為真理,對一個不斷變化的東西的信念根本就不是信念。邪黨文人的朝三暮四、出爾反爾必然會破壞掉人們殘存的對人性和美德的最后一點信心,鼓勵人們拋棄一切道德準則,以中共的好惡為好惡,把維護中共政權的存在當作第一需要。
本書一二章已經對學術界、宗教界、科學界的黨文人做了相當的揭露,我們在本節將重點剖析文學領域的邪黨文人是怎么歌功惡黨、改變中國人的善惡標準的。
廣義的文學包括各種文獻和著述,也包括狹義的文學作品。由于語言在人類文化系統里具有非同尋常的重要性,各大正統文化對語言和作為語言藝術的文學歷來非常重視。
中國文化是一種半神文化。古人相信,文章來源于至高無上的天道,因此說“文以載道”;文學可以提高道德、涵養性情,因此說“修辭立其誠”、“詩者持也,持人情志”。歷代的文人墨客,把文學創作當作“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以莊重誠敬的心態,創作了大量的優秀文學作品,這些作品其實正是他們清靜高尚的內心世界的反映。
中共作為一個控制人思想的邪教,對意識形態的重視,超越于往古來今一切政權之上。中共邪靈入侵之后,文學不幸淪為中共制造黨文化、灌輸黨文化的可恥工具。肯對中共俯首聽命的無行文人飛黃騰達,不愿放棄自己人格尊嚴的作家詩人即使免遭迫害,也被剝奪了寫作或發表的機會,只能在社會邊緣郁郁而終。
共產黨的文藝思想,由馬恩開其端,列寧承其緒,毛澤東總其成。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公開宣稱:共產黨“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這段殺氣騰騰的講話,拉開了中共利用其文人建立黨文化、操控中國人精神世界的序幕。從此,“政治標準第一,文學標準第二”,“文學為階級斗爭服務”,“全黨辦文藝,全民辦文藝”,“主題先行”等等,成為中共御用作家創作的指導原則。
1)用文學作品圖解中共的理論和政策
縱觀中國現當代史,不難發現,幾乎每一次中共發動的政治運動,都從批判某一部文藝作品或某一個文藝思潮開始。
四十年代的整風運動從王實味的《野百合花》開刀,五十年代一系列思想改造運動,從批判電影《武訓傳》、“紅樓夢研究”和所謂“胡風集團”開始,文化大革命用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祭旗,而批判電視片《河殤》則是“六四”鎮壓后的思想整肅的重要步驟。
另一方面,中共麾下的文人隨著中共的指揮棒翩翩起舞,用文藝作品圖解和吹捧中共的理論和政策,滿足不同時期中共的政治需要。
為了適應中共“土地改革”(剝奪地主土地)和后來的“合作化運動”(剝奪所有農民土地)的需要,文人們創作了《暴風驟雨》、《三里灣》、《創業史》,替中共掩蓋其在政治運動中殘酷的殺人整人、明火執仗的抄家和搶劫行為;為了丑化國民黨,把中共發起的內戰裝扮成“解放戰爭”,文人們創作了《林海雪原》、《保衛延安》、《紅巖》;中共需要美化“抗美援朝”,文人就寫《誰是最可愛的人》;中共需要圖解對資本家的“和平”改造,文人就創作《上海的早晨》;中共需要渲染中國人民“選擇”了共產黨,文人就創作《紅旗譜》;中共需要引導“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文人就創作《青春之歌》;中共要謳歌“大躍進”,全國就躍進出數以百萬計的偽民歌。
有人看了中共抹黑法輪功的電視劇后,說:“看了這個電視劇,我才知道為什麼要禁法輪功。”言外之意,不看這部電視劇,他還不知道為什麼要禁法輪功。中共的文藝捏造竟成了其“政策正當性”的依據,可見輿論灌輸在這場最新的鎮壓運動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實,歷史上中共煽動消滅“剝削階級”,用的是同樣的手法。雖然人們在生活中見到的地主(其實就是普通的土地擁有者)大多是勤勉誠實、熱心公益的厚道人,但經過中共灌輸,一提起地主,人們想到的一定是周扒皮、劉文彩、黃世仁、南霸天——這些用藝術手段捏造的地主形象。中共當年在其占領區用歌舞和戲劇教育士兵,很多戰士都是在看完《白毛女》等劇作以后,“激起了階級敵愾,燃起了復仇火焰”(周揚語),被中共“教育”成了“有覺悟的無產階級戰士”。